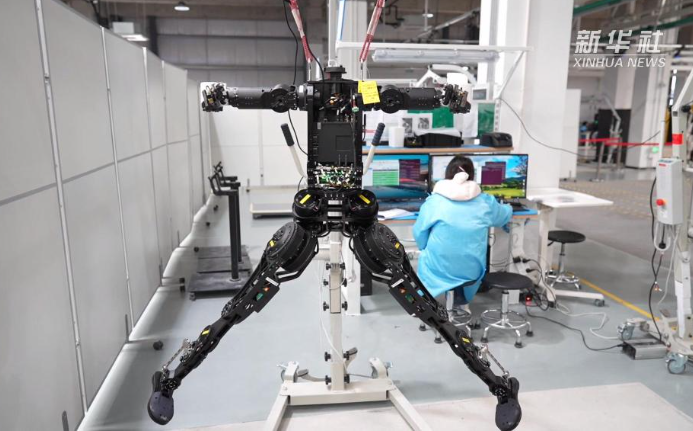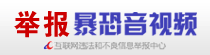天色還未大亮,屋里的暖氣片剛有了些溫暾氣息,小孫子便裹著毛茸茸的睡衣拱到我床邊,一雙亮晶晶的眼睛望著我:“爺爺,您說的秋天,到底藏在太原的哪兒呢?”我笑著摸摸他的頭。想著,得帶他去尋尋,用我這老太原的步子,用我這雙看慣了六十載并州秋色的老眼。
出門時,風是清冽的,像剛從汾河里撈起來帶著水汽的潤。陽光卻慷慨,斜斜地鋪下來,給高樓大廈的玻璃幕墻都鍍上了一層暖融融的邊。我們不坐車,就沿著人行道慢慢走。第一站,是離家不遠的文瀛公園。這里的秋,是有說頭的。湖面比夏日沉靜了許多,水色是種沉靜的碧,倒映著更高、更遠的藍天。幾株年歲最老的垂柳,葉子已染上深淺不一的赭石與金黃,但依舊柔柔地垂著,像不肯完全卸去綠妝的、矜持的姑娘。風過時,便有些許早凋的葉片,打著旋兒,飄飄悠悠地落下來,悄沒聲地歇在草地上,或是水面上,漾開極細極淡的漣漪。
小孫子蹲在湖邊,撿起一片完整的、邊緣已卷起焦黃色的樹葉,對著太陽看那葉脈,像看一幅神秘的地圖。“爺爺,這葉子好像您的巴掌。”他天真地說。我心頭一動。是啊,這葉脈,何嘗不似我掌心的紋路,也記錄著風雨和時光。我告訴他,我像他這么大的時候,文瀛公園周遭還沒這些高樓,湖顯得更開闊。秋天的傍晚,我常和玩伴來這里,聽那秋蟲最后的、拼盡全力地鳴唱。那時節(jié),空氣里飄著的,除了落葉腐爛帶來的、略帶酒意的醇厚氣息,還常常混雜著從附近人家飄出的煮玉米和烤紅薯的甜香。那是屬于我們那一代太原娃娃的、關(guān)于秋天的最樸素的嗅覺記憶。
離了文瀛公園,我們信步走上迎澤大街。這條太原的“長安街”,在秋日陽光下顯得格外寬闊、明朗。我指給小孫子看道路兩旁挺拔的國槐。它們的葉子正由綠轉(zhuǎn)黃,卻不是那種燦然的金黃,而是一種更沉穩(wěn)的、帶著綠意的淡黃,像上好的古玉。陽光從枝葉的縫隙里篩下來,在人行道上印出斑斑駁駁、晃動跳躍的光影。我說:“你看這些樹,它們看著太原一天一個樣兒。我年輕那會兒,這路還沒這么寬。如今,車流如織,聲音是沉悶而持續(xù)的轟鳴,是這座城市強勁的脈搏。這秋日的美,不獨在自然的變遷,也在這人世間靜默而巨大的生長里。
走得有些乏了,便往食品街拐去。一踏入食品街的牌樓下,空氣驟然就變得熱鬧而豐腴起來。這兒的秋意,是具體可感的,是能聞得到、嘗得著的。最應(yīng)景的,是用鐵皮喇叭吆喝著的“糖炒栗子”。那粗糲的黑沙裹著油亮的栗子,在鍋里“沙啦啦”地響,像是一首秋日的交響詩。我買了一包,熱烘烘地捧在手里,剝開一顆,金黃的栗仁又甜又面,小孫子吃得開心極了。這香甜暖熱,立刻驅(qū)散了清晨的那一絲微寒。我看著他,想起自己小時候,父親也曾在這相似的街巷,給我買過一包熱栗子。這滋味,這情景,竟像穿越了時空,重疊在一起。太原的秋天,便在這市井的煙火氣里,有了溫度,有了傳承。
穿出食品街的喧囂,我?guī)е鴮O兒打車來到汾河景區(qū)。沿著汾河岸漫步。如今的汾河,早已不是記憶中那條時而溫順、時而咆哮的“母親河”了。經(jīng)過整治,它成了一條波光粼粼的玉帶,平靜地穿城而過。岸邊的景觀帶修得極好,各種樹木高低錯落。秋色在這里,便有了層次。河水映著藍天、白云和兩岸斑斕的倒影,靜靜地流淌著。
走累了,我們便在親水平臺的石階上坐下。望著這悠悠的汾河水,我的話匣子便關(guān)不住了。我給小孫子講,古時候的太原,叫作晉陽,是李唐王朝的“龍興之地”。這汾河水,見證了多少英雄豪杰的往事,又承載了多少尋常人家的悲歡。我給他背小時候先生教過的詩句:“汾河不斷天南流,天色淡清涵暮秋。”雖然眼前的景致已大不相同,但那份天高水長的秋日意境,卻是相通的。我告訴他,太原的秋天,不止有眼前的這些。若再往城外走走,去到晉祠,那里有周柏、唐槐,秋日里更顯蒼勁;那難老泉的水,四季常溫,在秋天里會蒸騰起更濃的白汽,如夢似幻。還有崛圍山,秋深時,漫山紅葉,層林盡染,那才是大自然最酣暢淋漓的潑墨寫意。
“所以說啊”,我總結(jié)道,更像是對自己這大半輩子光陰的喃喃自語,“太原的秋日美,美在文瀛湖的沉靜,美在迎澤大街的變遷,美在食品街的香甜,也美在這汾河的悠遠。它不張揚,不炫目,像一壇老陳醋,得慢慢品,才能嘗出那歲月積淀下來的、厚實的滋味。它藏在每一片變了顏色的葉子里,藏在每一陣吹過街巷的涼風里,也藏在咱們太原人一日三餐的煙火日子里。”
“回家吧,爺爺,”小孫子拉起我的手,“我好像,聞到秋天的味兒了。”
我笑著站起身,牽著他溫熱的小手,踏著滿地的霞光,朝著家的方向慢慢走去。這一天的尋覓,于我,是溫習;于他,或許是播種。太原城這深沉而安詳?shù)那锶罩溃蠹s就是這樣,一代一代,在看不夠的風景與講不完的故事里,悄然流淌下去的。